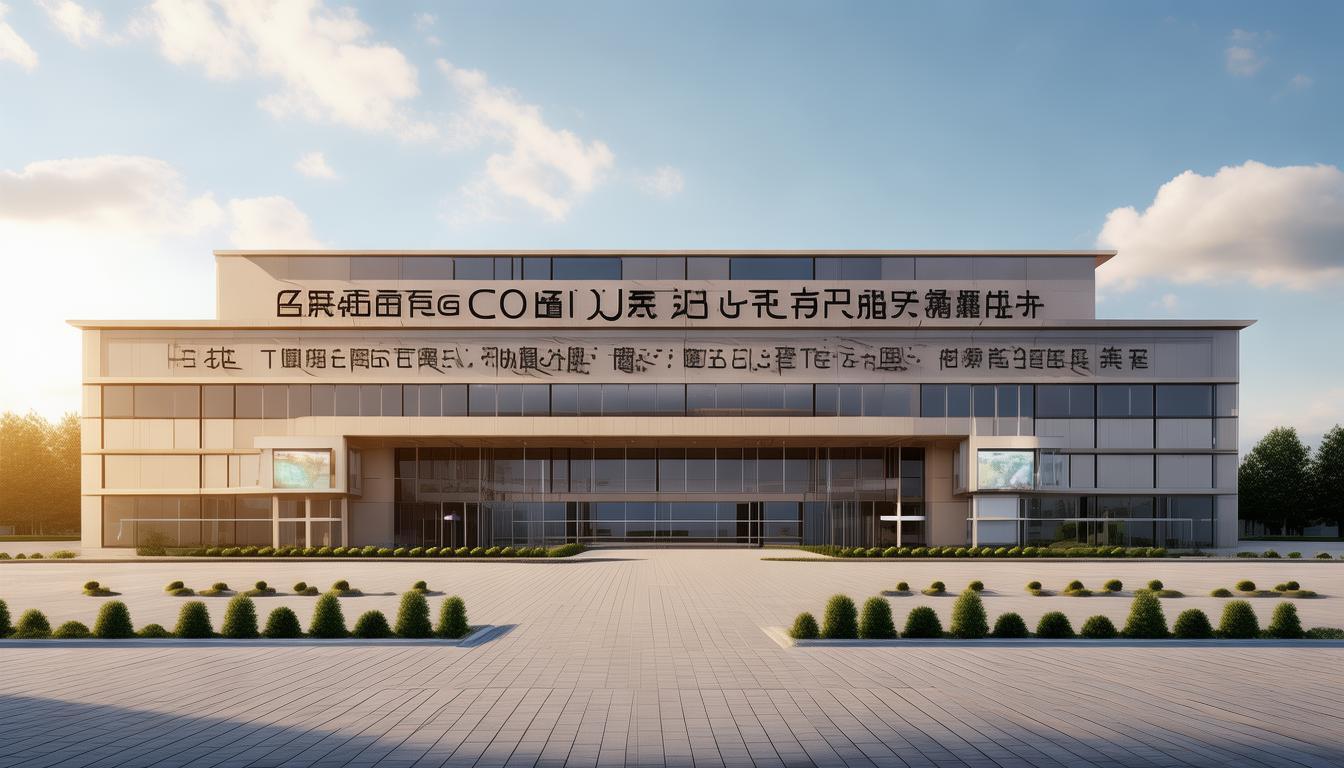长子口墓出土的玉人
长子口墓出土的提梁卣
长子口墓出土的带盖方鼎
长子口墓出土的骨排箫复原图
鹿邑县太清宫镇及其周边地带保存着众多历史文物和古迹,该镇周边还拥有一个龙山文化时期的古遗址——隐山遗址。1997年,为了探寻老子的故乡遗迹,深入挖掘鹿邑太清宫周边的古代历史,依据河南省政府的安排,在河南省文物局的精心指导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市、县级文物部门组建了考古队伍,对隐山遗址以及太清宫、洞霄宫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商周时期墓葬,并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经过考古专家对出土文物上的铭文进行解读,这座墓葬被正式命名为长子口墓。
初遇长子口墓葬
在1997年,该考古队以“追溯太清宫的古老历史”和“寻觅历代君王及民间对老子祭祀的遗迹”两大目标为核心,展开了深入的挖掘工作。
考古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遗址的核心地带已被民居和政府办公楼所覆盖,可供挖掘的区域极为有限,只得在房屋间的缝隙中进行挖掘,导致挖掘点显得分散且数量众多。经过勘查,他们了解到,在太清宫前宫前方大约100米的位置,存在一个略高于周边的黄土台地,这个地方长久以来被称作隐山。当地人透露,半个世纪前,此处遭遇了一场猛烈的暴雨,泥土中冲刷出了若干红色颗粒。经挖掘,发现了一个藏有朱砂的土坑,坑内还出土了铜碗、龙形玉佩、玉圭等文物。
考古人员对此线索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根据村民的说法,推测此处可能是一个用于祭祀的坑穴。于是,他们在隐山进行了考古挖掘。不久,他们发现了两座并排的车马坑,每座坑中都有四匹殉葬的马匹,它们呈面对面排列。经过分析,这些车马坑的年代与春秋时期相近。紧接着,考古团队开始在车马坑周边进行遗迹的探寻,不出所料,他们在居民的院落中找到了一块夯土筑成的墙壁,通过对比车马坑与夯土墙的相对位置,考古人员迅速锁定了接下来需要进行挖掘的具体区域。
考古发掘的惊人发现
发掘作业按部就班地推进,就在此时,探方中央显现出了生土与熟土的界限。考古团队沿着这两条界限的延伸方向持续挖掘,尽管已经挖掘了十几米,却依旧无法望见尽头。此刻,一位专家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墓道的迹象。若存在墓道,便暗示着墓葬的存在。
——这座墓葬的主人会是老子吗?
考古学者们认为,该巨型墓葬位于老子故乡太清宫遗址保护区内,而老子在任时的职务为守藏史,其地位相当于大夫。依据周王朝的礼制,尤其在春秋时期,诸侯及大夫去世后,其墓葬规格和祭祀仪式可提升一个等级,因此,按照这一习俗,大夫出身的老子得以按照诸侯的规格安葬,这在情理之中。
张志清,作为太清宫遗址考古发掘的负责人,指出,通过墓葬的结构、陪葬物品的搭配以及青铜器上的铭文,我们能够初步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该墓葬全长49.5米,属于南北双墓道的中字形大型墓葬。依据以往的考古发现,此类配备双墓道的大型墓葬,其墓主人当为王室成员、高级贵族或是某地的封疆大吏。在西周时期,只有天子或诸侯才有资格拥有墓道。由此我们可以确信,鹿邑太清宫的一号墓葬之主,其身份必定极为显赫尊贵。
张志清表示,正当众人满怀期待地准备深入挖掘之际,却出现了一个令人忧虑的情况,墓室入口处涌现出众多土质松软的盗洞。尽管这些盗洞让考古人员感到些许失望,但他们并未因此放弃继续探索的决心。
墓室深处,地下8米处显现出二层台的轮廓,台上存有两具人类的遗骸。这些遗骸表面涂有朱红色的朱砂,根据其摆放位置和姿态,可以推断出它们属于殉葬者。在西侧二层台上,殉葬者为女性,身高约1.7米,年龄大约在18岁上下。而在东侧二层台上,由于坍塌,殉葬者的下半身被压碎,性别无法确定,但大致推测年龄应在16岁左右。但考古人员根据经验判断,这具殉人很可能也是女性。
在考古人员持续挖掘的过程中,地下水源涌现,水面至墓底深度达3.2米。为排除积水,七台抽水泵持续运作,墓室内积水逐渐减少,大墓轮廓逐渐显现。尽管大墓的开口呈中字型,但坑底墓室却呈现空心十字形状。随着水位逐步下降,最先露出的是南边的主椁室,眼前映入的是8具殉葬者的骨骼,骨骼下方覆盖着朱砂。经过人骨鉴定,殉人都是年龄不大的青年人,甚至还有儿童。
随着积水完全退去,考古人员发现,椁室中还摆放着大量器物。
经过对墓葬的挖掘与整理,共计出土了2000多件陪葬物品。其中包括造型典雅的陶瓷制品,光泽透明的玉石饰品,工艺精湛的骨质工艺品,以及众多精美的青铜制品。其中,青铜器共有235件,依据其功能大致可分为礼乐器、兵器、工具、车马配件以及杂用器物等。在这批文物中,共有青铜礼乐器85件,根据其功能,它们可以被划分为炊食用具、酒具、水具以及乐器四大类。在这些炊食用具中,鼎的数量尤为突出,总计达到22件,其中又分为圆形和方形两种类型。
——墓葬主人并非老子
在对文物进行整理的过程中,考古专家们注意到这些青铜器与商周初期的风格高度契合,同时,老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他们依据墓葬的年代、墓葬的结构以及出土的文物等因素,得出了结论:“经过对墓葬年代、墓葬结构以及出土文物等方面的综合考量,我们否定了墓葬主人是老子的说法。”张志清如此表述。
根据殉葬习俗的观察,我们可以推测墓主人的身份属于商周时期的王侯阶层,这一点也成为了反驳墓主是老子的证据之一。张志清指出,在原始社会阶段,墓葬中就已经出现了殉葬的现象。随着社会进入奴隶制,厚葬的观念和仪式变得更加重要。在原始社会,殉葬现象多与祭祀仪式相关,而到了奴隶社会,殉葬现象则更多地用来彰显较高的社会地位。据史料所载,殉葬制度亦存在不同等级之别,《墨子·节葬》中提及:“天子之殉葬,人数众多者可达数百,少者亦数十;至于将军与大夫,人数众多者数十,少者仅数人而已”。在商朝奴隶社会达到鼎盛之际,殉葬现象在西周初期仍然相当普遍,但进入中期后,这一现象逐渐减少。春秋时期的哲学家老子,所见到的殉葬情形已极为罕见。
出土罕见多元文物反映时代特征
——墓葬年代为商周之际
根据对中字型多层大型墓葬结构的分析以及出土文物的特性,专家们推断该墓并非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时代,而是更早的商周时期。墓中出土的众多青铜器组合展现出商代晚期的风格,其中酒器尤为丰富,包括罍、尊、斝、爵、觚、角、卣、觯、觥等多种类型。众多器物的特征亦与商代晚期相吻合,例如鼎、尊、爵、觚等,这些器物与安阳殷墟晚期出土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同时,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西周初期风格的铜制器物,其中包括两件带有四个耳朵的铜簋,这类器物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仅在周朝初期出现。在出土的80多件玉器中,既有用于仪仗的玉戈、玉刀等,也有用作礼仪或装饰的璧、环、璜、玦以及柄形器和条形玉等,还有雕刻成虎、龙、牛、鹿、鸟等动物形象的玉器。这些器物的造型和雕刻手法既体现了商朝的风格,也展现了西周的特色。从以上特点可以推断其下限不晚于西周初年。

——青铜器多有铭文“长子口”,展示其他氏族与长氏的关系
墓中发掘出的铜制器物包括9个方鼎、11个圆鼎(其中6个为扁足形鼎,5个为鬲形鼎),4个方觚、4个方爵、7个圆爵、3个铜簋、4个卣以及4个觯。观察这些器物组合,可以推断墓主人的社会地位相当显赫。墓穴中存放的青铜制品大多刻有文字,经古文字学家鉴定,这些文字包括“长子”“长子口”“戈丁”等,其中以“长子口”出现频率最高,七八件铜器上都可见其踪迹,由此可知“长子口”即该墓的主人,“长”字象征方国,“子”字代表爵位,“口”字则是名字的标识。关于“长子”的铜器,流传下来的数量不少,几年前在湖北黄坡地区出土过“长子狗”鼎。然而,在豫东地区发现此类器物则是破天荒的头一回。经过深入分析,考古专家推断,此次出土的文物年代久远,据此推测,鹿邑地区很可能是长氏族早期活动的主要区域。
太清宫所在区域位于中原商周王朝与东夷、淮夷的接壤之处。在商朝末年,长氏方国曾是商朝的附属国。在帝乙、帝辛时期,为了对抗东夷,商王朝将关系紧密的长氏方国派遣至现今的鹿邑县东部,或许长氏方国原本就占据了这个地方。武王灭掉商朝之后,长氏方国依然承担着守护周王朝东部边界的重任。长子口之所以被认定为“东夷后人”,关键在于其墓葬中发现了13名殉葬者,而据学术界共识,殉葬习俗在商周时期是东夷部落中普遍存在的,因此可以推断,长国与东夷之间应当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这座墓葬呈现出鲜明的商代风格,其中青铜器以盛酒器具为主,墓中陪葬有13具人骨,墓室底部设有腰坑,腰坑中陪葬有1人1犬,这些均符合商代墓葬的习俗。尽管该墓的埋葬年代可能已至西周,但墓主与商朝的联系紧密,他很可能属于殷商时期的遗民。
殷朝的遗民居于商朝末期至周朝初期,当时在商朝担任高级贵族,而在周朝也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地位。长氏家族与商朝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甲骨文卜辞中记录了长氏曾向商王献上乌龟作为贡品。此外,通过已发现的西周铜器上的铭文,进一步证实了长氏在周朝时期已经向周朝表示臣服。
长氏一族相传是东夷少昊的后代,他们曾在商朝时期负责弓箭的制造。在殷纣王统治时期,辛甲作为长氏的贵族成员,后来他选择投靠周武王,并在讨伐殷纣王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长子口墓可能是辛甲本人或其子孙的安息之地,该墓位于西周初期,是派往太清宫附近驻守的高级贵族墓葬。
通过对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进行解读,我们得知墓主的名字是“长子口”。医学专家对墓主人的骨骼进行了详细鉴定,推断其年龄大约在60岁左右,性别为男性。长子口身为国家的君主,这一点在墓葬的构造、埋葬的习俗以及陪葬的物品中均有明显体现。具体来说,长子口的墓葬呈“中”字型,设有南北两个墓道,墓室为“亚”字型,整体结构非常规整。
亚字形墓室仅见于商代的大型墓葬,此类墓葬通常拥有四条或两条墓道,墓主身份非商王即王室成员,亦或是地位显赫的诸侯国君主。据资料记载,目前尚未发现拥有四个墓道的西周时期的大型墓葬,这一疑问或许需待西周王陵的发掘才能得到解答。在西周时期,尤其是西周晚期,墓葬道上的基葬显现了明显的等级差异。同样,在西周初年,这一现象也得以体现。长子口墓的墓葬形制和规模在已知的西周墓葬中位居首位,这一事实足以说明长子口的身份和地位超越了普通诸侯,从而推测其为长国之君。
随葬品的数量、种类以及组合方式与墓主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紧密相连。在长子口墓中,出土的85件青铜礼乐器数量显著,远超目前所知的商末周初墓葬出土的文物,由此可窥见墓主的身份地位之高。
方形青铜器在殷代代表着统治阶层的权力与尊贵。在长子口墓中发掘出的方形铜器,其种类和数量在商周时期的墓葬中尤为突出。学者们根据对方鼎大小三种类型的分类,发现长子口墓出土的方鼎中,有四件属于中型,五件则被归类为小型。通常情况下,若墓葬中出土至少两件中型鼎,墓主往往为方国国君,偶尔也有王室中的高级官员。长子口墓中发掘出了九件方鼎,这表明墓主长子口并非寻常的方国国君。换句话说,长氏家族在那时仍拥有相当强大的势力。
——酒器类器物应有尽有
殷商末期,嗜酒之风盛行。这种风气不仅是殷商末期的一种社会现象,更是导致商朝覆灭的众多因素之一。通过出土的众多酒具和乐器,我们可以推测,墓主人在世时,当是一位生活豪放不羁,热衷于轻歌曼舞的人。
该墓中藏有的酒器种类繁多,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其中,酒器类器物琳琅满目,包括用于饮酒的爵、觚、角、觯,以及用于盛酒的尊、觥、卣、罍,还有用于温酒的斝,取酒的勺,以及用于盛酒或调和酒水的盉等。特别是“长子口铜提梁卣”的出土,成为了该墓最具特色的随葬品之一。这件文物属于西周初期,其整体高度为30厘米,口径的直径约为13.5厘米,而短径则是10.8厘米。器身呈椭圆形,顶部带有拱形的扁提梁长子县古代遗址,梁的两端设有环,与器身两侧的半环形耳套相连接。在盖的内壁和器的底部内壁上,都刻有“长子口”三个字的铭文。当文物出土时,器内含有大约1000克的液体,经过检测确认,这些液体是酒。
——出土我国最早的骨排箫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音乐考古资料,其中还包括了我们国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骨制排箫。
张志清在介绍时,情绪依然高涨。排箫,作为古代常见的乐器,在《诗经》中就有“箫管备举”的记载。过去考古发掘中,曾有三处出土了排箫,包括竹制和石制的,它们均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在这三处遗址中,出土的排箫数量最多只有两件,但长子口墓中却出土了五件。而此次新发现的骨制排箫,是用禽兽腿骨制成的,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排箫实物。我国的研究揭示了早期管乐器并非以竹为材料,而是以骨为原料,这一发现将我国制作排箫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并为《诗经》中提及的“箫管齐备”提供了真实的物证。
长子口墓中出土的乐器,包括排箫、铜铙与石罄,若将它们组合使用,便能构成一个由至少8人组成的乐队。在商周时期的墓葬中,首次发现如此丰富的乐器组合。墓中出土的排箫、编铙以及磬等,恰好印证了中国古代乐队中吹奏乐器与打击乐器相结合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音乐的审美追求。这一发现,对于我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证据。
——造型独特的玉人彰显了长国族群的特点
出土的玉器中,其中一件玉人形象独特,形态诡异。此玉人头部似虎,置于墓主身旁。其耳呈半圆形,口阔大张开,露出锋利的牙齿,上下各有七颗,眼睛呈长圆形,目光锐利,如同虎视眈眈。从虎头以下,则呈现出人身形象,身体前倾,呈跽坐姿势,双手置于膝上,五指向下,足趾未露,似有鞋覆盖,身着一袭衣物。玉人背部呈蹲状,眼睛圆睁,突出有神,虎耳变成了人的耳朵,背部则塑造成人形,双臂伸展成双翼,双腿则塑造成足部。昂首挺胸长子县古代遗址,怒视前方。
该文物通过将人类形态与猛禽、凶猛野兽的形象相结合,象征着战神之尊,同时也从侧面揭示了长氏族群的特征。
此器巧妙融合了虎首与人身,独具匠心,工艺精湛,通体装饰以阴线云纹,仅在双臂纹饰等少数地方采用单线阴刻,形象逼真,栩栩如生。长子口墓中,此类圆雕作品实属罕见。它不仅生动展现了西周初期璀璨夺目的玉雕技艺,更为我们研究周人的坐姿、服饰、头饰、发型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长子口墓葬考古发掘意义深远
长子口墓葬的挖掘成为商周时期考古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特别是该墓葬位于豫东平原,地处远离商周王朝核心区域的边缘,正处于当时东夷、淮夷统治力量的交汇之处,这使得其重要性尤为凸显。在1998年,长子口墓葬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荣誉奖。
国家文物局前局长张文彬对隐山遗址的挖掘工作以及长子口墓的历史价值给予了高度赞誉。他指出,鹿邑长子口墓的考古发现是近年来的一大亮点,其在学术领域的重大意义,在某些层面甚至可与渑池仰韶遗址、安阳殷墟等著名发掘相媲美。
太清宫镇在商周时期曾是一座关键的城池与军事要地,到了春秋时期,它又成为了厉国的国都。正因为如此,人们常说这片土地孕育了我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家老子,这一说法并非巧合。
长子口墓始建于西周初期,墓主人的生平足迹横跨了商朝与周朝两个历史时期。在淮河流域范围内,长子口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为宏大的商周时期墓葬。此次长子口墓的考古发掘,再次让我们领略到了周口这片土地的瑰丽与辉煌。
在墓葬中,一批新颖的器物被发掘出来,尤其是种类繁多的青铜礼乐器,这充分展现了当时工匠们丰富的创意和卓越的工艺水平;骨制排箫的出土,不仅将我国排箫的起源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同时也为我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那些随葬的精美玉器,玉质纯净、工艺精湛,明显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色;在出土的117件陶器中,其中一些器物形态独特,如四件大口尊,其喇叭形口、筒状深腹、平底的设计,在以往的大型商周墓葬中实属罕见。
出土的器物展现了文化的丰富多样性。长子口位于豫东平原,隶属于淮河流域,这片土地在新石器时代便成为了我国东西南北多个主要文化区域的交汇点,其文化特征充分体现了多元性。在商朝晚期,鉴于这里是商王朝与东夷统治区域的分界线,其文化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东夷文化的影响。商王多次东征,而长子口地处东征路线的必经之地,因此,这里的文化特征应当与这些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该墓出土的物品兼具西周风格特征,同时融入了商朝的某些元素,展现出鲜明的地方风格。
古文献中记载,太清宫地区在春秋时期是厉国的领土,该地曾出土西周初期长氏贵族的墓葬,这引发了我们的思考:长氏家族与厉国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在周昭王时期,长氏贵族的墓葬在湖北省亦有所发现,这究竟是氏族迁徙的结果,还是军事南征的痕迹?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未来的考古发现中,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和丰富,才能得到解答。(记者 王晨 通讯员 李全立 唐涛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