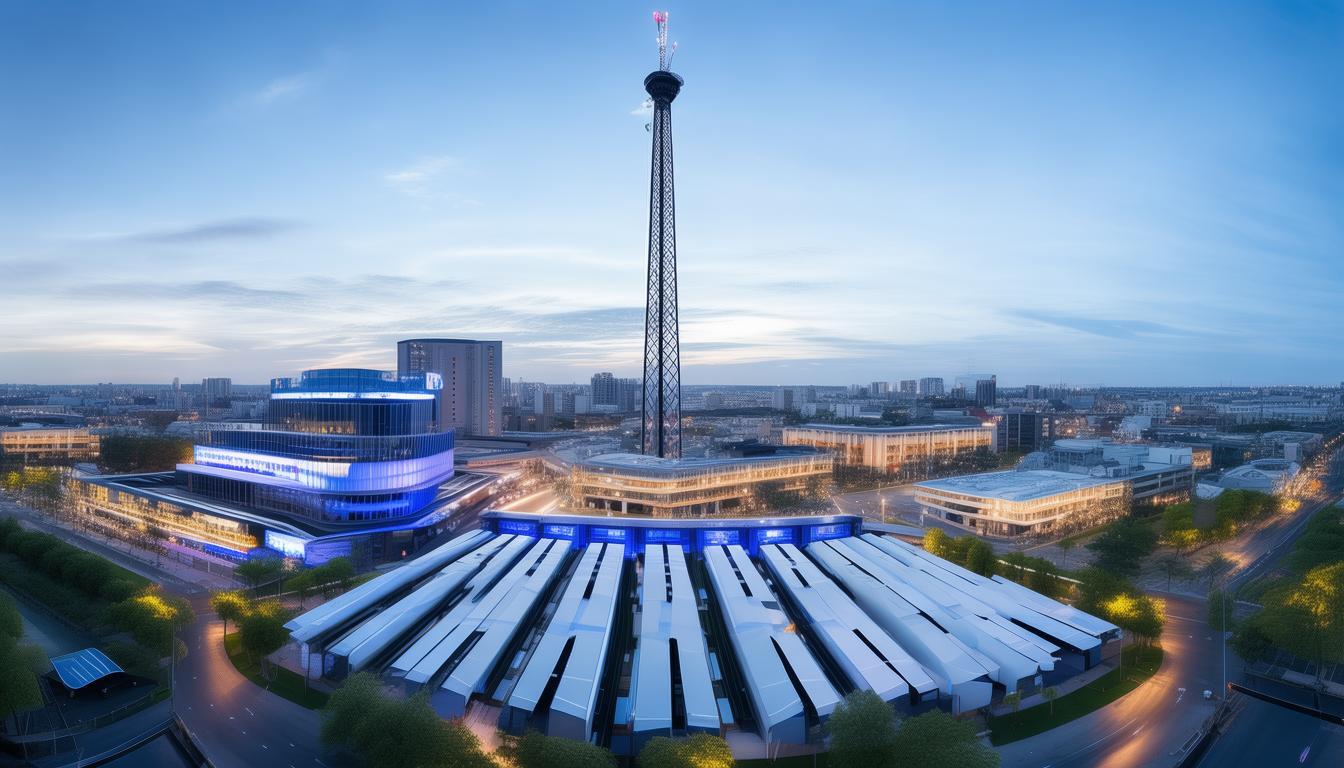它会来吗?会的。它会来吗?会的。
这段台词出自塞缪尔·贝克特的代表作《等待戈多》,他是荒诞派戏剧的先驱,亦为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关于他的获奖简介,可以这样表述:贝克特凭借其独特形式的小说与戏剧创作,为现代人带来了精神上的鼓舞与振奋。贝克特在文学领域,擅长描绘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幻无常与微妙细腻,同时兼具诗意般的清醒与连绵不断的内心独白。
我满怀期待地守候着戈多的到来,然而这份等待似乎永无尽头。在漫漫长夜中,我仿佛置身于地狱般的深渊,时刻担心在那些缺乏星光的黑夜里迷失方向。起初,这仅是一场等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等待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习惯。 —— 《等待戈多》
今年正值贝克特百年诞辰。在上海国家舞蹈中心上演的这部舞剧《May B》,由法国编舞家玛姬·玛汉于1981年首度公演,它让我们得以更加直观地领略到当代艺术的另一种独特表现形式。肢体语言的生动演绎与戏剧场景的激烈碰撞,运用抽象且极具震撼力的舞台手法,细腻刻画了群体与个人的形象,揭示了人类生存的荒谬性、时间的束缚性以及人性的多重矛盾,对贝克特荒诞派文学中的存在主义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即便在44年后的今天,这部作品依旧被视为具有前瞻性的先锋之作。
尚未踏入场地,便已预感今夜将有不凡的体验。随着演出临近开始,门前依旧挤满了等待的人群,保安正分批次引导观众入场。于是我们,这些观众,在门口被有意识地聚集,又被随机地引入,宛如水珠。开场前几分钟,剧场内弥漫着些许不安,随后灯光熄灭。然而,并未立即亮起,一片寂静,寂静,或许是因为大家怀揣着对大师作品的敬畏,都安静了下来。非常寂静,一片漆黑,人们的内心与四周都趋于平静,随后,弦乐声缓缓奏起,灯光逐渐亮堂起来。映入眼帘的是宣传照上那般如石膏般的人物群像。共有十位,他们是人,还是石膏像?他们身上覆盖着厚重的石膏,据说多达四层,黑绿白三色的身体颜料,甚至可能混有石膏粉末。初看之下,你几乎无法辨别他们的性别、年龄、头发颜色以及种族等,他们身上缺乏任何单独个体的细节特征。

它们宛若石雕般坚固,同样挺拔,形成了一幅群像,典型的群像,你或许会这样想。然而,伴随着音乐的节奏,他们开始缓缓移动,对,移动,有的三人一组,有的五人一组,以小碎步缓缓挪移,显得笨拙而充满探索,毫无美感可言。他们艰难地前进,又退后,仿佛映射了生活的真实面貌。他们相互交错,偶尔分道扬镳,动作有时协调一致,有时又显得漫无目的。他们的表情极其夸张,时而低声细语,时而大声咒骂。他们时而群起而攻之,相互搏斗,时而紧紧相拥,深情接吻。地面上散落着许多白色粉末,不知是过往行人所留,抑或是他们十人留下的痕迹。那些坚硬如石膏的塑像终将化为尘埃,这满地的尘埃,是否隐藏着更多无法察觉的辉煌,那些早已逝去的荣耀?
据传,这十位角色均源自贝克特的创作,我个人最深刻的体会来自于《等待戈多》这部作品对文本的启示,该剧集中展现了“等待”这一象征着无意义生活存在的困境。舞台上,舞者全身涂抹着白色粉末,身着破烂衣衫的流浪汉,通过机械式的步伐,反复的跌倒与爬起,以及快速奔跑后突然的定格,生动地描绘了人在时间流逝中徒劳无益的循环。紧接着,观众席上方传来了哨声,背景音乐则仿佛是铁皮鼓的节奏。每当哨声和鼓点声响起,舞者们便会迅速整队,或是变换舞姿,仿佛置身于行军列或是机械动作之中,生命似乎在这一刻被节奏所主宰,沦为一种空洞的循环。他们抹去了年龄和性别的界限,化身为无名的符号,将个人的经历提升为一种全人类共通的生存象征。
蛋糕的分享环节本应充满温馨,然而,当人们意识到每过一年,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岁,这种对时间无情流逝的感知,是否还能让你感到愉悦?再者,当一群人围坐一起,原本温馨的生日蛋糕分享和拥抱亲吻,却瞬间演变成争夺、咒骂和迁徙的暴力场面,这恰恰是人们最熟悉的爱恨交织的生存画卷。它揭示了人类既渴望彼此连接,却又常常陷入冲突的永恒矛盾。舞者手提皮箱,依次排列前行,彼此间伸出援手,他们从舞台上退去,亦或是步履蹒跚地在风雪中挣扎前行,这些画面深刻揭示了战争给群体带来的创伤。他们扭曲的身体和沙哑的嗓音中迸发出的毫无意义的词汇,正是战争的象征,也是流亡生活留下的创伤印记。皮箱这一元素,让我联想到日本艺术家盐田千春的装置艺术作品。这个箱子实质上是一个盲盒,里面装满了时代Labubu的种种印记,承载着主人的回忆与记忆,既有欢笑也有泪水,宛如潘多拉的盒子,既孕育着希望,也可能一无所有。它,就如同等待的戈多。
这部舞剧的创新之处在于,它突破了传统形式的限制,对舞蹈语言进行了颠覆性的创新。玛汉将雕塑(以白粉塑造的肉体如同泥土中的雕像)与贝克特的戏剧台词和荒诞剧情相结合,舒伯特的音乐则与哨声和喉音的拼图相互融合,从而使舞蹈不再仅仅是技巧的展示,而成为了集多种观念于一体的艺术表达。《Mayb》译为《可能贝克特》后,其英文名称更贴近《可能Maybe》或是《可能存在》,其中“B”或许代表“Be”。这部作品通过舞蹈和身体的表达,揭示了贝克特作品中人类存在的本质。在荒诞的等待中,人们沦为时间的奴隶,而通过微小的抗争,如分享、亲吻、拥抱等,为生存注入了微不足道的光辉。如来自白垩纪元的斑驳舞者,是历史的伤疤,也是人性的纪念碑。
玛汉通过超越舞蹈舞台的创作品,展现了他独特的舞台美学,完美地诠释了贝克特的作品,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于生命意义和生存目的的深刻思考。我们目睹了彼此的一生,奔波劳碌,却常常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最终以无疾而终的方式结束。